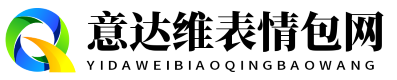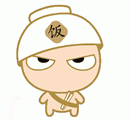我被拉进N个老年人群看到一堆开心表情包和很多
“陈光来了,咱们玩吧!” 下午两点,“暖心家园”微信群里有人喊道。 136人组成的“温馨家园”微信群瞬间活跃起来。
“大家好,我给大家发一首歌曲,叫《一路向北》!” 群友发布了一段视频。 视频中,一位留着温柔披肩发的上海阿姨戴着耳机,唱着一首歌。 紧接着,群里又添加了一段视频:一位穿着红色皮夹克、戴着黑色贝雷帽的大妈,声音充满激情地唱着《昨夜的星星》。
“喜欢它!” “听起来不错!” “被歌声陶醉了!” “拍拍你的小手!” 其他小组成员发送了免费的表情符号。
一周前,记者被白万清老师拉进了四个老人组。 这群人都是记者父母的老年朋友,他们来自上海各地。 第一次进入这些群体时,记者被他们的热情吓了一跳:“欢迎,欢迎”“欢迎排队”,一堆我父母辈的专属表情向记者飘来; 当群活跃起来的时候,微信群里几乎瞬间就充满了歌唱表演、舞蹈表演、笛子演奏。 群里的朋友争先恐后地发布了在家里拍摄的视频。 真是热闹极了。 疫情期间,家里的生活很困难。 这群老人在群里载歌载舞,演绎了一段非常时期的“云端生活”。
他们在“云”上不带感情地载歌载舞,热情富有感染力
伴随着悠扬的音乐,一位戴着粉色围巾的阿姨翩翩起舞。 她轻盈飘逸,身材比很多40多岁的中年人都要好; 一个穿着红色衣服和白色裤子的男人。 叔叔伴着二泉映月的音乐,翩翩起舞。 叔叔的舞步还很陌生,但他沉浸其中的热情却很有感染力。 这是“暖舞团”中的一个普通场景。
原来,“暖心舞团”的团员很多都是平时一起跳舞的舞者。 他们曾在社区、疗养院进行文艺演出,颇有名气。 然而,疫情来临时,他们再也不能聚在一起跳舞了。 于是,舞蹈队“东方”队长想出了一个办法,让大家在“云”上跳舞:每天预约下午两点,团员将舞蹈视频上传到微信群供大家欣赏。 交流,一方面也督促自己不要浪费自己的舞蹈功力。 群里还有一位退休舞蹈老师在“云”上进行指导。 看完其他舞者的视频后,他会一一点评:“一定要准确地跟上音乐的节奏,在家多听。” “耸耸肩,抬起头,多练习。” 前几天,春暖花开,大家都有点“蠢蠢欲动”了; 但大家都严格遵守纪律,听从指挥。 “当我们能再次聚在一起跳舞时,我们必须听政府的安排。现在我们不能聚在一起,所以我们可以把舞蹈安排在‘云’上。” 这几天,队里都在讨论排新的舞蹈,等疫情过去了,我们再聚在一起表演,就能拿出新的节目了。
下午三点,在“京华暖心笛小组”,小组成员正在互相交流群友发布的《小镇故事》笛演奏音频:“吹得很好,节奏很很稳定,语气也很好听。” “你们。” 要知道,她利用业余时间练习,甚至睡在床上在肚子上练习手指。”“她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,学习她不服输的干劲。”组长“ “范范”是最活跃的,他把群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:每天安排一个小时的集体教学,笛子老师点评大家的作品;每隔一段时间就安排主题表演,比如“云”上的聚会同样,大家呈现自己喜欢的节目;每隔一天,还有厨艺交流,“饭饭”也经常发布自己在家锻炼的视频,每个动作都简单易学,很有用,很多群友也跟着视频在家锻炼。
“暖心之家”、“老邻居团”也热闹非凡。 这两个群的成员并不像前两个微信群那样都是“职业玩家”,但表现同样热情。 “唱得不好也没关系,大家玩得开心就好。” “申生”是“老邻居团”的召集人。 该团伙80余人,都是长宁区一条老胡同的邻居。 我们从小就认识。 老胡同30多年前搬迁,邻居四散。 我们五年前联系并成立了这个小组。 “平时大家都会偶尔开个聚会什么的,但疫情来了,聚会没法办了,就开始在网上互动。除了唱歌,还交换信息,互相劝告。”呆在家里吧。”“申生”说道。 。
欢乐的歌声和欢笑的背后,有一个悲伤的故事
“我是组长,我想活跃一下气氛,想出一些有趣的话题,让大家积极参与。在这个组里,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。” 电话里,“凡凡”的声音充满了幸福。 “忙碌而快乐”正是疫情以来群内不少老人的生活现状。
然而,在这些欢乐的歌声和欢笑的背后,却隐藏着悲伤的故事。 在记者被拉入的四个小组中,三个小组是“失去独生子的家庭”的小组。
2018年,白万清承担了市妇联“让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不再孤独”项目,邀请社会各方组织“温馨家园理事会”。 理事会组织服务失独老人,逐渐吸引了一批失独家庭的老人——“暖心之家”成立。 他们经常为老年人组织线下聚会,根据老年人的特长组织兴趣小组,发现文艺骨干,于是舞蹈队、笛队就诞生了。 这些艺术团队定期一起排练节目,扩大了老人的朋友圈,丰富了老人的生活。
“范范”是“暖心笛队”的队长。 长笛队于去年5月成立,现有成员42人。 年龄最小的60岁,最大的76岁。“只要愿意学的都可以报名参加,我们免费提供长笛,免费教。” “范范”年轻时是单位的文艺骨干,也是一个热心人。 “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,当别人快乐的时候,就是我们最孤独的时候。” 11年前,“凡凡”唯一的儿子因病离开了他。 这么多年,他都是一个人生活。 “范范”说,他不敢参加同学聚会,也不敢与其他老人交往。 许多家庭在失去独生子后会离开原来的居住地,只是为了远离悲伤的地方和过去的场景。 对于失去独生子的家庭来说,与处境相同的人在一起是一种安慰。
对于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,为老人组织活动并不容易。 老年人的心理障碍必须慢慢克服,消除社会偏见不可能一蹴而就。 笛子队成立初期,由于一些场地管理者听说他们来自失去独生子的家庭,所以找不到合适的场地,将他们拒之门外。 一路走来,有各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坎坷。 但他们也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。 静安寺街静华居委会原本有一支笛子队,但由于部分队员年龄较大,部分队员家庭搬迁,该队无法组建。 听说暖心笛子艺术团找不到活动场地,居委会书记就主动提供居委会活动室给他们排练,支持他们的演出。 队员们感动不已,将暖心笛队更名为京华暖心笛队,成为社区文艺力量。 他们还带着京华居民参加活动。
特殊时期,最需要互相关心、互相支持。
疫情发生以来,暖心之家和各个暖心特战队的老人牵动着白婉清的心。 “失去独生子的家庭成员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。 现在他们都呆在家里,不能外出,也不能聚集。 生活节奏被打乱,他们容易焦虑。 对疫情的困惑和恐惧会增加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。 负担。 这个时候,他们最需要的是互相关心,互相支持,抱团取暖。”白婉清说道。
春节还没过,几个微信群就活跃起来了。 “暖心家园理事会”成员及各团体业主每天用微信发布积极向上的文章,鼓励大家响应政府号召,积极响应,团结抗疫。 他们还不时地想出一些智力开发的文字游戏来丰富大家的业余时间。 生活。 随着疫情的变化,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,都希望疫情快点结束。 我看到“京华暖心笛子团”每天都在表演笛子表演。 场面十分热闹,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忘记了烦恼。 白万清与理事会成员商量,在各组组织一些活动,利用微信开展“宅在家里才艺表演”,并在疫情结束后进行考核。
理事会成员和团长在团内组织活动、活跃气氛、传递正能量的同时,也默默关心团员的心理变化。
“向大师”是“暖心之家”的理事会成员、组长。 有段时间,他得知群友每天要去医院打静脉注射,但家里没有口罩,他心里很着急。 “香猪”和群里的几位老人收集了一些口罩,送给了他。 也有抑郁的人意识到他的心理变化。 “相爷”在群里找到一些自己熟悉的老朋友,经常发私信鼓励他“不要念旧,好好生活”。
在“京华暖心笛组”,有的组员觉得自己表演不好,不敢上传视频、音频,也不怎么说话。 “范范”经常在群里@他们,鼓励他们“点赞”也可以。群里都是老年人,有的不太会用视频拍摄。委员们和组长发动善于运用的人互相教导。
如今,团里不少小姐姐每天出镜前都会精心打扮,还用美美的照片来展现自己的美丽。 一旦发布,就会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好评。 “我们只是想鼓励这种做法。我们要振作起来,把它漂亮地展现在大家面前。” 项朱说道。
(范范、申生、东方、向珠均为化名)